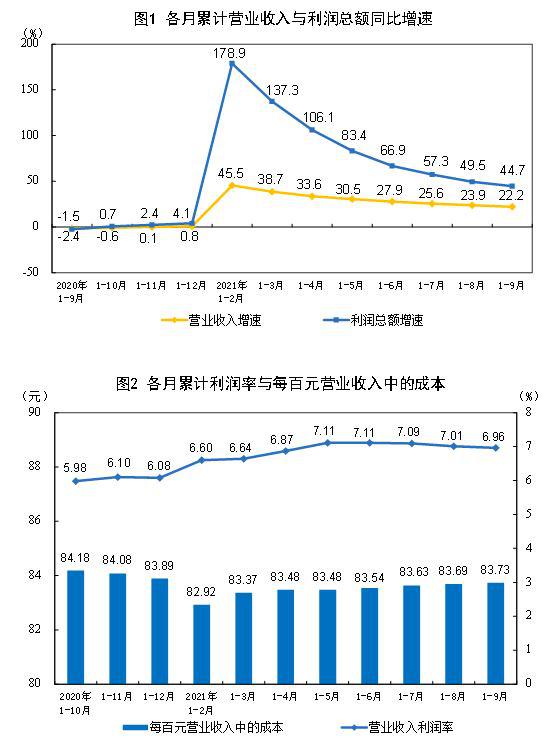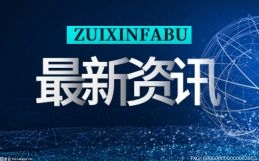(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我国最负盛名的经济史学家之一、中国经济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与推动者——傅筑夫先生(1902—1985)的著作《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五卷本)即告付梓。两年多来,笔者有幸作为这部270余万字巨著的编辑团队成员之一,感触良多,尤其是对傅先生的大匠风范及其作品中所彰显的中国气派,更感回味无穷。这样的经历于一位编辑的职业生涯而言,可谓可遇而不可求,其妙难以言表。以下为笔者在编辑傅先生这部皇皇巨著过程中的一些体会和感悟。
一者,其著纵横千年,格局恢弘,凸显中国学术气派
有学者提出,此前有关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史,虽有些断代性的研究成果,但没有人作贯通性的研究,唯有本书是一部通史性成果。诚如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魏明孔教授所言,傅筑夫先生在书中全面探讨了自西周至宋代2000多年间中国经济发展、经济制度演变的历程,并在充分占有材料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就中国经济史的分期以及一些重大问题的性质和原因等提出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见解,填补了我国经济史领域的一项空白,也实现了傅先生“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夙愿。
以笔者担任责编的本书第二卷(秦汉三国卷)为例,全书共十章,凡70万言,分别从经济区及其变化和发展、土地制度和土地问题、劳动制度、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经济与货币制度、货币财富的形成与积累、经济波动、经济政策等方面,全面展现并分析了秦汉三国时期的经济特征和发展变化。书中史料详实,论点鲜明,论证严谨扎实,许多观点之于今天仍有很强的启发性和解释力,对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运行和发展变化规律,则更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对此有学者深有感慨道:“众所周知,同行中没有人能从根本体系上对傅先生提出批评。”
傅筑夫文集(第一辑)《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秦汉三国卷)书影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傅先生在本书的创作中,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并结合丰富生动的中国经济史案例,给出了富于中国特色的科学论证与结论。不仅如此,傅先生还通过中国经济变迁的历史实际,以事实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仍以本书“秦汉三国卷”为例,经笔者粗略统计,在近600页的书稿中,引用马克思经典理论的即达百余处,足见作者已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思想“如盐入水”般地融入了书中。
除此之外,傅先生之下笔也堪称一绝。
一是言必有据,文必有引,信息量极大。据张汉如教授在《学贯中西博通古今:傅筑夫的学术道路和思想研究》一书中的统计,傅先生论著中所引证的史料和当代考古资料达万余条,平均每万言引证史料约33条。对此魏明孔教授指出,这充分体现了傅先生学术根基之深,也足见其养心治学的擎括功夫与老而弥坚的探索精神。二是文笔雅白,“雅白”者,雅致之白话。这是笔者在编辑此书时有感而发而“造”的一个词,因文笔其雅而不史,白而不野,品之如饮甘露,十分畅怀。三是条分缕析,逻辑精妙,有如推理佳作,拨开层层迷雾,透视中国历史,读之十分过瘾。
二者,其学立足中国大地,专精博览,沙里淘金
傅先生的学术功底和文字功底,无疑与其足称楷模的治学精神是分不开的。学术界都知道,傅先生治学有“三绝”。
一曰博闻。其一,极佳的古文修养。魏明孔教授在为本书所作序言中提到,1924年,傅先生入读北京师范大学理化系,在旁听梁启超、鲁迅、黄侃、钱玄同等名师的课后,心有所属,便于第二学期转入国文系。在这里,傅先生系统学习了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选修了古典文学、文艺理论和外国文学名著等。此后,他又在鲁迅先生的建议与指导下从事中国古代神话的研究与资料搜集工作。这样的训练,无疑为傅筑夫从浩瀚古籍中搜集、整理与甄别资料,为后来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二,很高的外文修养。对英、日、德文的熟悉,是傅先生学贯中西,及时汲取国外最新成果的得力手段。其三,极好的经济理论修养。魏明孔教授在本书序言中提到,1937—1939年,傅先生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专攻经济理论和经济史,这为他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中、欧比较的广阔思路和视野。在伦敦大学期间,胡寄窗先生也恰在这里留学,他们时常在一起探讨经济史方面的学术问题,二位最后都成为享誉海内外的经济史、经济思想史领域的学术大师。
二曰强记。在许多人眼里,傅先生记忆力惊人,他直到80岁高龄时还能随口背诵大段的古文。傅先生自己也说:“在我还没有认识文字以前的幼儿时代,就由祖母口授背诵了《唐诗三百首》。”然而,傅先生之强记绝非只凭好记性,而更多来自“烂笔头”。据说傅先生一生积累了约220万字的学术资料,这使他的著作材料翔实,立论有据。有学者认为,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傅先生积累的经济史资料居全国之冠是没有异议的,而这还不包括此前因各种原因而丢失的大量明清时期的资料。傅先生之“烂笔头”功夫还被他大加推广。魏明孔教授在本书序言中提到,1939—1945年,傅先生在重庆国立编译馆任编纂,在傅先生的发起和主持下,大后方开展了规模庞大的中国古代经济史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编译馆当时给傅筑夫先生配备了4名辅助人员以及10余位抄写员。抗战胜利前夕,第一轮资料搜集工作告一段落。课题组用纵条格厚纸做卡片,用毛笔抄写的资料多达数大箱,这些卡片分纲列目,分类条编,每章均有简明扼要的说明与分析。可以说,正是这一张张资料卡片,日后撑起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巍峨大厦。
三曰笔勤。身边人曾说,傅先生在80高龄时,写起东西来,仍下笔如有神,效率极高。这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五卷本著作,正是傅先生以76岁高龄由南开大学调往北京经济学院(即现在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主持国家科学发展规划中的重点项目“中国经济通史”后,在6年多的时间里完成的。可谁又能知道,在这6年多里,这位古稀老人是如何惜时如金的。
傅筑夫文集(第一辑):《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全5卷)书影
三者,其人笃行唯实,饱含家国情怀
如果说以上“三绝”主要指的是傅先生治学之勤奋严谨,那么在傅先生之等身成就之中,不可或缺的还有治学者之笃行唯实与家国情怀。20世纪初,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彼时,青年傅筑夫先生已开始关注社会变革,并将学业方向转向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史。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傅先生也毅然步出象牙之塔,他正视当时的社会现实,投身经济学领域,并自觉在治学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
傅先生有鲜明的是非感,强烈的爱国心。其大学期间的一位同学,曾与日本侵略者有过不正常关系,傅先生对他十分厌恶。20世纪80年代初,该人回国后,特来拜访老同学,但傅先生冷落了他,令其败兴而去。
傅筑夫先生除去是学术宗师外,还是一位独树一帜的教育家,而他对教学的高见是在长期的教学第一线的实践与教学管理工作中得出的。魏明孔教授在本书序言中提到,1930—1946年,傅先生先后在河北大学、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东北大学任教,讲授经济学概论、农业经济学、中国经济史等课程。1947年8月,傅先生任南开大学教授,同时讲授中国经济史、外国经济史两门课程。新中国成立后,傅先生在南开大学又增开了“《资本论》研究”这一课程,其间亦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任教,直至1978年调往北京经济学院。在半个多世纪的从教生涯中,傅先生有数十位弟子已先后成长为我国经济史研究与教学的领军人物,今天仍活跃在学坛的经济史大师、新中国经济史的奠基者之一赵德馨教授,就是其中一位。正如魏明孔教授所言,“傅筑夫先生深刻影响了四代学人,且今后还会深远影响国内外学术界,尤其是经济史学界”。
纵览傅先生数十年的教学心得,有以下几个方面令人印象至深。
一曰德才兼育。傅先生对学生的品德教育是溶在教学过程的点滴之中的。他指出,“学生既要有起码的科技道德,又要有正确的治学态度和方法,以防止不正之风——为名利不择手段。要制定法规,以防毒害青年和污染学术空气”。
二曰教研相长。傅先生强调教学要与科研结合,科研要为教学服务。他说:“据外国先进经验,高校中的教学人员同时也是科研人员,教一年后带着问题到研究所解决,再回到教学中去,并将本学科的最新成就体现到教学中去。学校中的研究所如不为教学服务,就会牵制教学力量,科研就会无意义……”
三曰以慢为快。听过傅先生讲课的人都说,傅先生的课有事实,有材料,有分析,也有活跃气氛的“花絮”,总能给人以深刻印象。他主张,教学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全面能力,因此要“慢为快”:不必填鸭式地重复书本内容,而是应在内容之外的背景上,在内容之中的难点上下功夫,讲透彻;这在局部上好像很慢,但讲透一点即带动全面,在全局上是快的。
傅筑夫先生的这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五卷本)曾于20世纪80年代由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一晃三四十年过去,此次重新出版,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挖掘自家宝藏的重点成果之一。为此,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成立专班,由总编辑牵头,组织骨干编辑,历时三年有余,始告功成,并于近期面世。书中新增补的数万字《校勘记》,权作我等后学向傅先生的致敬。
谨以此文,作为对傅筑夫先生的无尽缅怀与追忆,也作为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经济史研究及其出版、传播的祝愿与展望。
(作者潘飞,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编辑,博士,副编审)
关键词: